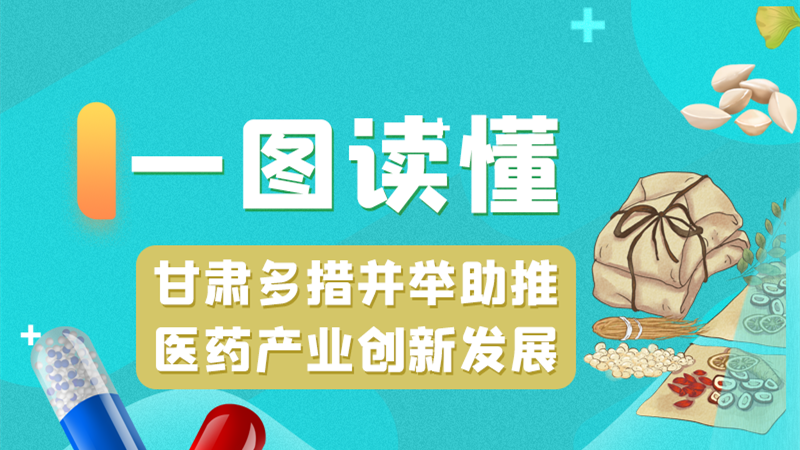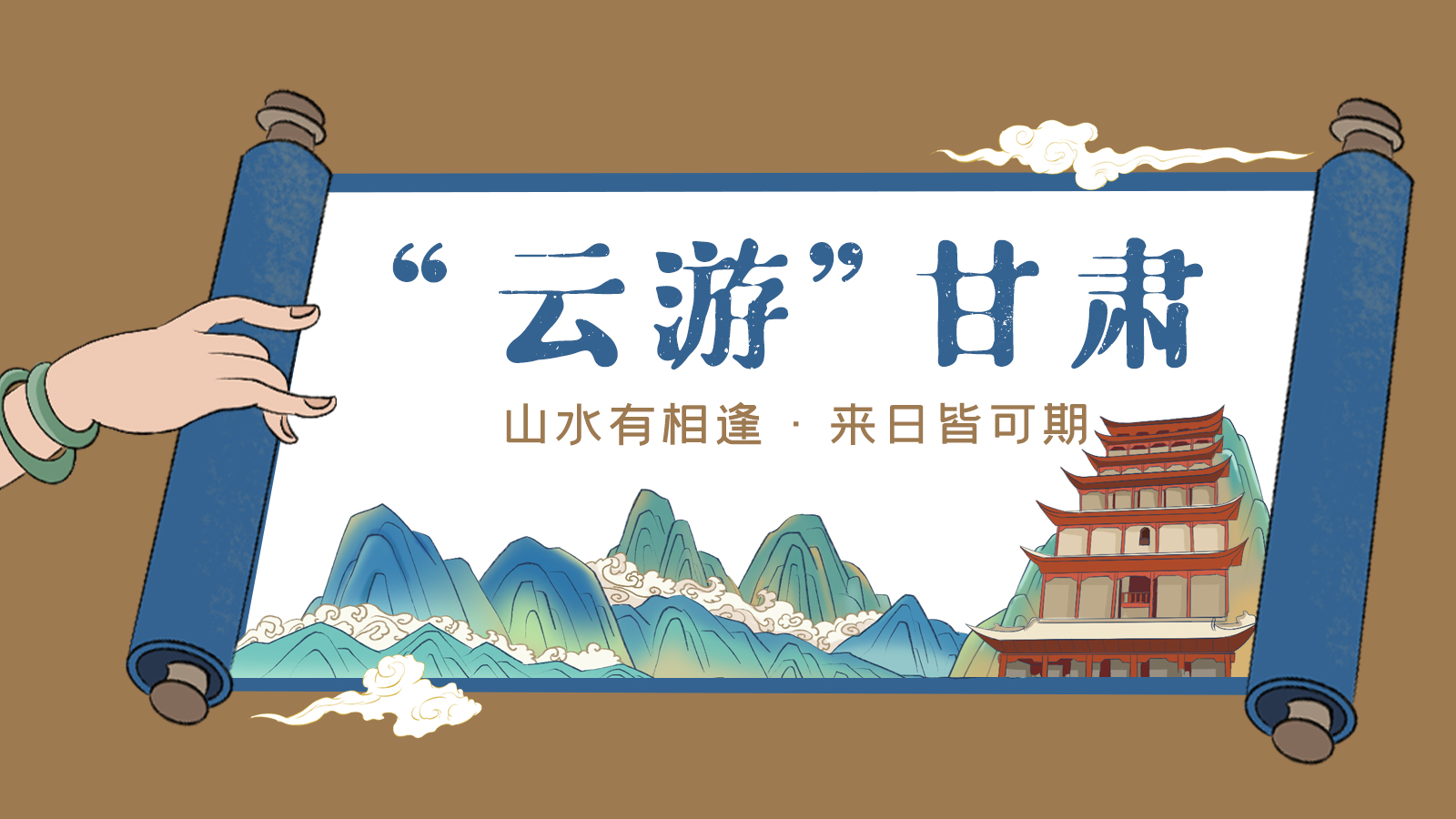收受他人財物是受賄罪的核心構成要件,沒有收受財物的行為,就難言“權”與“錢”之間具有可交易性,自然不能認定行為人構成受賄犯罪。實踐中,收受他人財物一般表現為對財物的實際占有,但特殊情形下,行為人雖然未實際占有財物,卻仍可視為收受了他人財物,進而構成受賄犯罪。
實際控制財物。刑法理論和實務部門普遍認為,應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收受他人財物”要件的認定標準。行為人客觀上雖未占有財物,但對財物有控制權的,可認定為收受了他人財物。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收受財物的認定標準,符合受賄罪的立法精神,同時有利于恰當處理受賄罪實踐認定中的相關疑難問題。對實際控制財物的認定,理論界和實務部門經常討論的一個問題是,行受賄雙方約定由行賄人代為保管財物的情形。筆者認為,此種情形下,認定受賄人對財物是否有控制權,應重點考察兩方面:一是行受賄雙方的關系。一般而言,只有雙方關系密切,相互信任,且受賄人對行賄人的行為具有一定把控力時,受賄人才能保證行賄人所保管財物的安全性,才能達到對財物隨用隨取的支配狀態。反之,則難以認定受賄人對財物具有控制權。二是財物所處的狀態。如果財物屬單獨保管,受賄人獲取財物沒有其他障礙的,則一般應認定受賄人對財物具有控制權。如果財物沒有單獨保管,受賄人難以隨時支取財物,或者即便是單獨保管,但受賄人獲取財物仍需要依靠其他外力的,則表明受賄人對財物的控制力存在一定障礙,此時一般不宜認定受賄人實際控制了財物。但這種情況下,仍可能認定為受賄未遂。
代為支付財物。實踐中,有些受賄案件,行為人并未實際占有、控制賄賂物,而是基于自身事由授意或認可請托人代自己支付財物,這種代為支付財物的行為,亦應認定為行為人收受了他人財物。例如,在劉某受賄案中,劉某利用職務之便為丁某謀取利益后,安排丁某為其疏通關系解決相關事宜,為此,丁某花費錢款共計4000余萬元。法院最終認定上述錢款系劉某的受賄所得。行為人授意或認可他人代為支付財物,實質上是將自己應當實施的行為和支付的費用等,利用職權讓他人去完成,仍屬于一種權錢交易。因此,收受他人財物,并非一定是受賄人親自接手財物,安排請托人代為支付財物的行為,也屬于收受他人財物。
免除既定債務。某些受賄案件中,國家工作人員或其指定的第三人與請托人形成債權債務關系后,請托人基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行為而免除相關債務的,屬于一種變相的權錢交易,應視為國家工作人員實際收受了財物。例如,在重慶市北碚區委原書記雷政富受賄案中,肖某以不雅視頻相要挾向雷政富借款300萬元,雷政富授意私營企業主明某向肖某出借該筆款項,明某表示同意,并以公司名義借款300萬元給肖某。借款到期后,肖某在資金充足的情況下拒不歸還借款,雷政富知情后表示愿意代肖某償還,明某表示無須歸還,雷政富予以認可。法院經審理認為,明某出借300萬元給肖某,以及放棄對該筆借款的追索,均是基于雷政富此前利用職權為其公司提供了關照,并希望繼續得到雷的關照。盡管明某免除債務的行為客觀上使肖某獲利,但這完全源于雷政富與明某之間的權錢交易和雷政富最終對該財產的處分意思。因此,該300萬元款項名為肖某與明某公司的借款,實為明某與雷政富之間的權錢交易款,應認定雷政富實際收受了該筆錢款。
轉讓不良債權。在經濟活動中,當國家工作人員或其關系人作為債權人通過正常渠道難以實現某項債權時,如債務人失蹤、破產等,為使自身利益不遭受損失,國家工作人員有時會利用職權將相關不良債權轉移給請托人來承接。這種轉讓債權的行為看似屬于一種民事活動,實則可能具有權錢交易的性質,因此,應作實質性判斷。具體而言,可從國家工作人員及承接人雙方的主觀認識,以及債權的可實現狀況兩方面進行判斷。如果國家工作人員和承接人均認識到債權本身難以實現,所謂的債權轉讓實質上就是基于國家工作人員職權行為的一種利益輸送。同時,在綜合考察債務人的現實情況、資產狀況等因素之后,能夠以“一般人”的標準得出債權確實難以實現的,此時,應認定國家工作人員轉讓債權的行為系一種變相權錢交易。相應地,請托人因承接債權而產生的財產損失即為國家工作人員所收受財物的數額。(作者: 李丁濤)
- 2022-08-10同為退休后領取“顧問費”為何定性不同
- 2022-08-10基層治理呼喚青春力量
- 2022-08-10夯實黨和國家監督體系的“四梁八柱”
- 2022-08-10《芯片和科學法案》:以競爭之名行遏制之實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