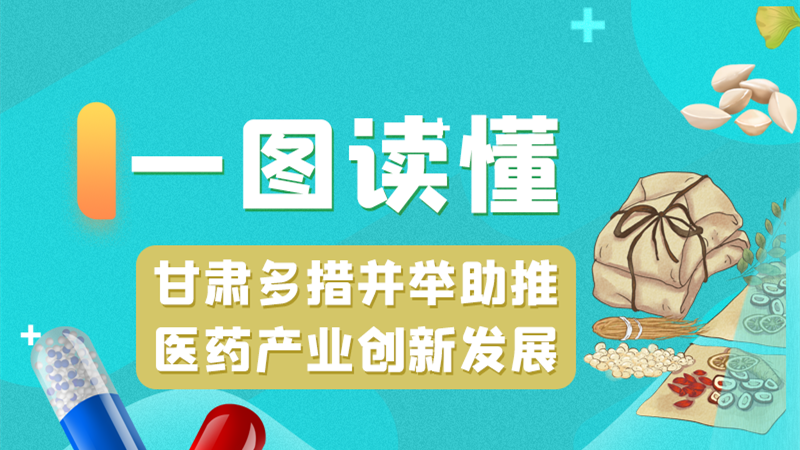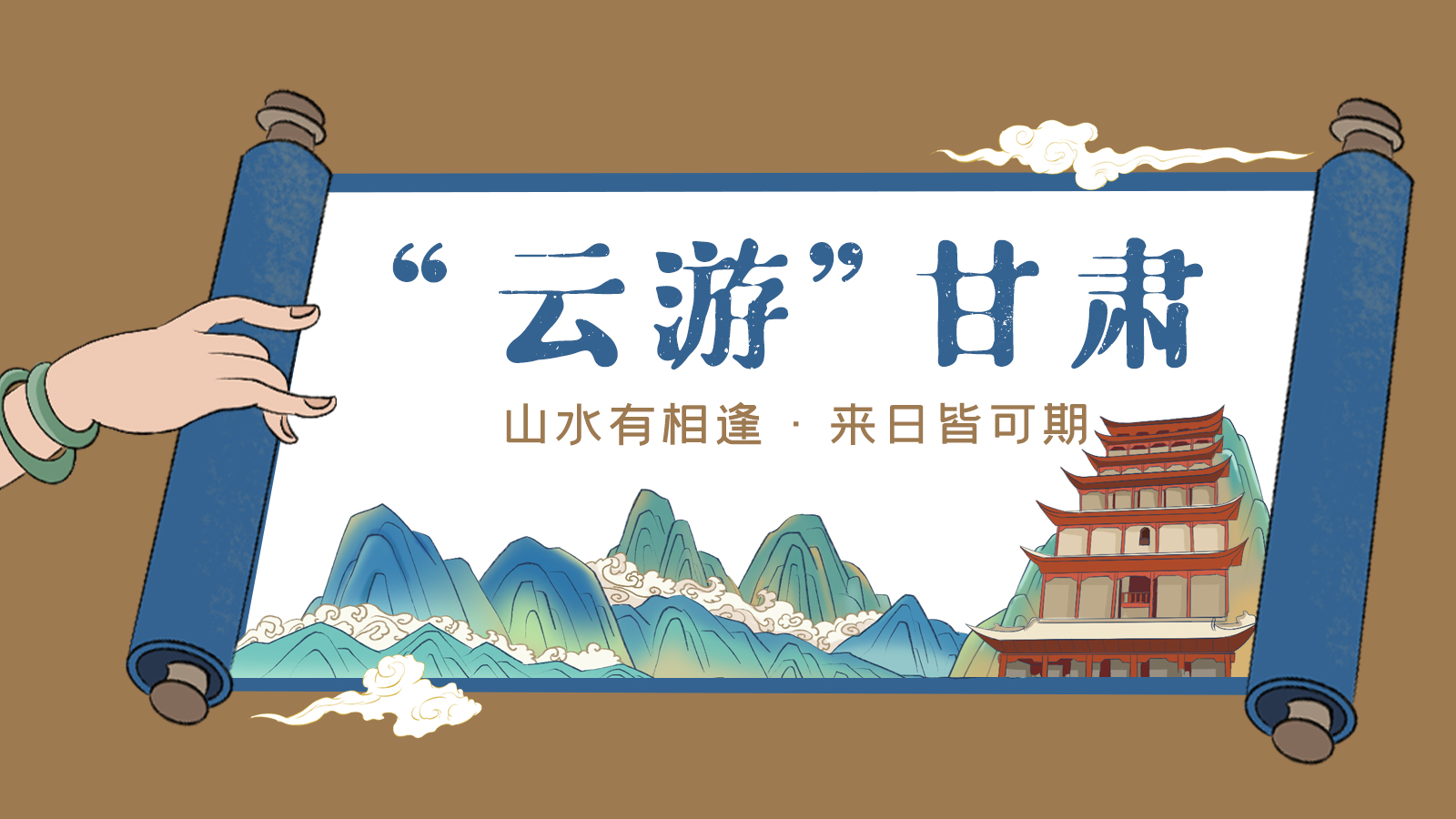我何以對母親河一往情深?
□莊電一
“天下黃河富寧夏”,這是700萬寧夏人民耳熟能詳的一句話;“寧夏依黃河而存在,憑黃河而發展,借黃河而興旺”,這是寧夏有識之士的共識。
作為一名生活在黃河旁,一直吮吸黃河乳汁的新聞記者,我對這條母親河一直滿懷感恩之心,對寧夏因黃河而興的歷史,我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我始終以飽滿的激情贊頌黃河,也滿懷深情地呼吁保護黃河,深入挖掘神秘的黃河文化,對黃河的事務都給予了密切關注。
引黃灌溉,對寧夏具有特別的意義,所以有必要大力宣傳。正因為如此,我對這方面格外用心,許多稿件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和感染力。在長篇通訊《水興,寧夏興》中,我在開頭就寫道:“水興,則寧夏興;寧夏興,必先興水!”開宗明義就說出了水與寧夏的關系,也點出了黃河對寧夏的重要性。而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的《黃河玉帶育明珠》,更是將黃河造福寧夏、寧夏開發利用黃河的方方面面都寫到了。
展現黃河對寧夏的寵愛、對寧夏的影響、帶給寧夏的福利,也是我著墨較多的。在采寫這些稿件時,我總是格外用心,寫起來也格外用情,發表的篇幅、位置也都很好。在通訊《水!水?水?!水……——寧夏中部干旱帶盼水、集水、引水、節水紀事》中,我飽含深情地寫出了寧夏中部干旱帶人民與水的故事和生活的艱辛。在此之前的1994年,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率領全國政協委員中的水利專家考察寧夏并與寧夏達成共識,決定在中部干旱帶紅寺堡興建扶貧揚黃灌溉工程并形成一份將改變20萬貧困群眾命運的政協提案,我對此作過多次報道,其中,《全國政協2027號提案》還在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等部門主辦的全國“同心譜”征文中獲得了一等獎。1996年5月11日,扶貧揚黃灌溉工程開工,我及時作了報道。在紅寺堡開發取得歷史性成就時,我以“入眼平生幾曾有”為題作的報道,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
我還關心水利建設中的問題。寧夏引黃灌區深得灌溉之利,但水價卻長期在低位運行,水利部門難以為繼。了解到這個情況后,我在《光明日報》上直言不諱地發出呼吁:《入不敷出的水價該動一動了!》。自治區第二年就調整了灌區水價,我為此又作了后續報道《寧夏灌區水價終于調整了!》。在寧夏引黃灌區,長期存在大水漫灌、縱水入溝的現象,為改變這種狀況,我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方面,我對這種現象給予批評;另一方面,又對節水措施的推廣、農民用水觀念的改變給予了肯定和引導:《發展節水農業迫在眉睫》《旱地集水微灌創奇跡》《敢叫秋雨潤春苗》《寧夏今年少引黃河水4.5億立方米》《水稻節水增效大有可為》《引黃灌區節水還有沒有潛力?》《寧夏灌區農民用水變“吝嗇”了!》《寧夏農業灌溉正告別“大鍋水”》。針對外界對寧夏引黃灌溉的質疑,我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長達半版的述評:《寧夏該不該種植水稻?》,正本清源,解疑釋惑。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一些不肖子孫肆意糟蹋母親河、不珍惜母親河資源,我為母親河代言,譴責了那些錯誤的行為:《治理黃河水質污染刻不容緩》《黃河再也經不起如此污染了!》《母親河面臨斷乳危機》《造紙企業成為黃河寧夏段污染大戶》。此后,經過國家治理黃河水質大為改善,我也作了及時報道,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勵。
退休以后,我又采寫了大量與黃河和引黃灌溉有關的通訊和特寫:《黃河岸邊的神秘村莊》《湖泊多處鳥來多》《紅寺堡:千古荒原變綠洲》《珍珠灑滿黃河灘》《千年唐徠渠,今日換新顏》《一半勾留是此湖——“塞上湖城”銀川素描》《黃河在這里撒下串串珍珠》《因黃河水滋潤而豐饒的土地》等。寫這類稿件,我總是格外用心、格外用情。
我雖然沒有親自參加建設黃河、保護黃河的勞動,但我利用自己的工作為保護母親河、合理利用母親河、讓母親河不斷流和少污染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自我感覺做得還不夠,也還想再作一點有益的貢獻。“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對母親河的恩德、寵愛和奉獻,我無以回報,所以內心總是誠惶誠恐的。
(作者系光明日報社駐寧夏記者站原站長)
- 2022-08-03讀書,長夏的一服清涼散
- 2022-08-03在愛爾蘭的留學時光
- 2022-08-01古詩里的七夕
- 2022-07-28從池塘到文學,荷花別樣美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