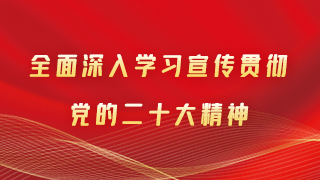一年前,在第十三屆文化中國講壇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郁綴引名句用典故,講述了“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大唐“詩仙”李白傳奇的人生歷程,生動賞析其一生中的多篇傳世名作,將詩人的豪放飄逸與清新自然展現得淋漓盡致。一年后,程郁綴再次登上第十四屆文化中國講壇,這一次,他“請”來了另一位詩歌大家,他是李白的忘年之交,是杜甫筆下的“飲中八仙”。他生逢盛世,仕途順遂,是唐代的長壽詩人,他就是自號“四明狂客”的賀知章。
賀知章一生官至秘書監,人稱“賀監”。在程郁綴看來,在賀知章的人生經歷中,其與李白的交往不得不提。
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42歲的李白已頗負盛名。經好友吳筠推薦,李白得到了皇帝的賞識,奉詔入長安,翰林供奉。據唐代孟棨《本事詩》記載:“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那一年,賀知章虛歲84歲。賀知章見李白英姿豪俊,又請其所寫之詩文。李白拿出《蜀道難》以示之。賀知章讀未竟,贊嘆不已,驚呼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稱李白為“謫仙”,并“金龜(唐代三品以上官員的一種配飾)換酒”,一醉方歸。而“謫仙”也成為李白一生中最喜歡、并引以為豪經常自稱的一個雅號。
賀知章去世后,李白懷著悲痛的心情寫下《對酒憶賀監》,深情地回憶道:“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翻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
和李白與賀知章的忘年情誼一同留香千古的,還有賀知章的詩歌作品。程郁綴分享的第一首賀詩是七言絕句《詠柳》:“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春天來了,詩人以欣喜的目光看著新柳的主干如碧玉妝成。絲絳,就是旗幟上的垂縷。第一,很美。碧和綠乃是生命的本色,是大自然中植物的基本色。第二,層次分明。詩人從柳的主干寫到柳條,再寫到柳葉,層次非常清楚。第三,這首詩題為詠柳,實則頌風。后兩句是詩人心口相商,自問自答:那一排排整齊、鮮亮、透嫩的綠葉,是誰剪裁出來的呢?是大自然這位能工巧匠,揮動二月春風的剪刀精心剪裁出來的藝術珍品。”程郁綴如此賞析道。
詩人越是將春柳寫得美好,越是在烘托春風惠物之功,因為這一切美好都是春風帶來的。風無形無色,既摸不到,也抓不住,只能借綠柳來彰顯,通過詠柳來贊頌,可謂是潑墨在柳而歸趣在風。全詩字里行間充滿著對自然的愛、對生活的愛、對美的愛,成為詠柳詩中的名篇。
除了對自然之美的贊頌,對故鄉的感懷也是賀知章創作生涯中的重要題目。古往今來,不知多少詩人寫下懷念故鄉的詩歌,但其中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還要數賀知章的《回鄉偶書二首》。其一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程郁綴說,這首詩便是好在無一字說家鄉“好”,卻每一個字都流淌自詩人的內心深處。
《回鄉偶書二首》其二的光芒雖不如其一耀眼,但同樣語淺意深、耐人尋味。詩曰:“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
賀知章的故鄉毗鄰鏡湖,鏡湖便是如今浙江省紹興市柯橋區的鑒湖。詩人離開家鄉已久,無情的歲月風霜已經消磨了村里大半年紀大的親人。唯有門前的鏡湖水,春風一起,又如往年一樣春水渙渙、碧波蕩漾。程郁綴說:“故鄉的風景依然,但人事不再,這種物是人非的感慨,引起了不同時代人們的強烈共鳴。水是故鄉甜,山是故鄉青,月是故鄉明,人是故鄉親。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何時,不管境況如何,都不應忘記自己的故鄉,并把熱愛故鄉的淳樸感情,升華到熱愛祖國的理想高度,為百姓的幸福、祖國的富強和民族的興旺,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陳鼎
- 2022-11-22今日小雪|圍爐溫酒,歲月溫柔
- 2022-11-22清代《大學》詮釋的學術特質
- 2022-11-22《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記錄的周人故事
- 2022-11-22說“真淳”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