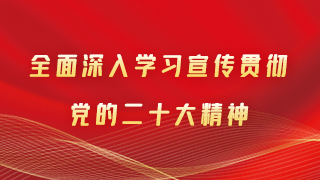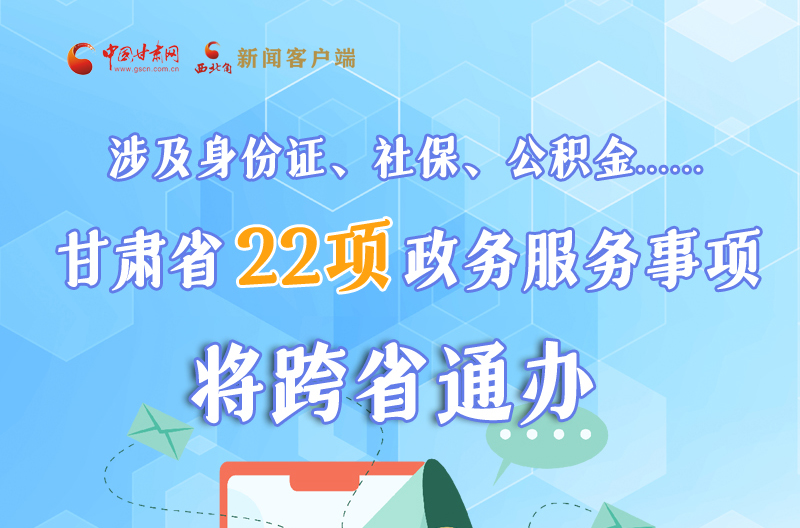作者:李敬峰(陜西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緣于“其(王陽明)與朱子抵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故《大學》遂成為“宋明六百年理學家發論依據之中心”以及“理學發展的風向標與晴雨表。”這就將《大學》在理學史當中的肯綮地位提解出來。而在宋、元、明、清理學發展的四個時期,清代無疑是《大學》詮釋史上大師云集,著述宏富,學派林立,新見紛呈,成就斐然的一代。其學術特質主要有:
《禮記》之《大學》與《四書》之《大學》并行
《大學》原本屬于《禮記》中的一篇,后在朱子那,與《論語》、《中庸》和《孟子》合刊為《四書》,并隨著朱子學上升至官學地位,《大學》亦隨同四書成為家弦戶誦的經典,以至出現毛奇齡所謂的“朱子有《大學》,五經無《大學》”的學術局面。而這一情形到明代的時候有所松動。明代的祝允明指出:“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本朝因之,非敢妄議。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故愚以為宜以《學》、《庸》還之禮家。”揆諸史料,應該說祝允明是較早發出《大學》重返《禮記》的學者,然囿于朱子學的強勢地位,祝氏這一主張雖在當時并未引起多大影響,但其所涵具的象征意義要遠遠大于其實際意義。而后明清之際的郝敬、陳確、王夫之等在祝氏的基礎上邁出實質性的一步,直接在其禮學著作中全文錄入《大學》,尤其是隨著乾嘉漢學的興起,“《大學》璧回《禮記》”蔚然成風,且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由乾隆皇帝親自主持編纂、刊行的《禮記義疏》直接收錄《大學》,可謂是從官方的角度肯定了《大學》返歸《禮記》的主張,其所產生的蝴蝶效應,至清廷解體依然存在。但必須指出的是,《禮記》之《大學》的出現,并未取代《四書》之《大學》,反倒是形成相峙并存的態勢。但“由于沒有出現一個權威的注本(包括《禮記》在內),《大學》、《中庸》僅僅是在形式上重返《禮記》而已。”也就是說,《四書》之《大學》仍然稱雄科場,而《禮記》之《大學》則雖有官方支持,但并不具備足以取代《四書》之《大學》的實力。無論如何,《禮記》之《大學》與《四書》之《大學》雙軌并行確是清代《大學》詮釋史上的一個特色所在。
《大學》詮釋階段性特征明顯
一般而言,對于斷代學術史的理解和把握,不約而同地會關涉到學術的分期問題。晚清的皮錫瑞將清代經學劃分為三個特征明顯的時期:以漢宋兼采為主的清初、以漢學為主的乾嘉時期和嘉道以后,以今文經學文主的時期。皮氏這一論斷大致是把握住了清代學術的主流特征。而后的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又明確提出三變說:有清一代學術,初期為程朱陸王之爭,次期為漢宋之爭,末期為新舊之爭。就從學術特質而論,梁啟超的理解與皮錫瑞大致相同。王國維則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國初之學術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稍晚的錢穆則將清代學術劃分為四個時期:一是晚明諸遺老時期;二是順康雍時期;三是乾嘉時期;四是道咸同光時期。龔書鐸主編的《清代理學史》則將清代劃分為三個時期:一為順康雍時期;二為乾嘉及于道光中葉;三為道光中葉至清結束。從這些代表性學者的論述中可見,對清代學術的劃分主要是三期說和四期說,后者較之前者主要的不同是更為關注明清之際這一階段,意在為清代學術的發生厘清源頭。但無論何者,清代學術特征的變化用梁啟超的三變說較為清晰和準確,故本文此處采納梁啟超之論。而從較為宏觀的角度而言,清代的《大學》詮釋史在輪廓上與梁啟超、王國維所論保持一致,在學術主旨上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即清初主要是回應朱、王之爭,中期隨著王學的衰熄,旨趣轉變為漢、宋之爭,而晚清則經世致用特征明顯,顯豁出王國維所謂的“新”。
古本《大學》研究最為鼎盛
眾所周知,《大學》是四書當中牽涉爭議最多的經典,僅僅是版本問題就一直紛紜不斷,難有定論。僅臺灣學者李紀祥考證的兩宋以來的主要改本就有46本,而在這眾多版本中,占主導地位的無非是古本《大學》(鄭玄)與今本《大學》(朱子改本)。而隨著陽明心學的崛起,古本《大學》開始與今本分庭抗禮,并在明清之際“回歸原典”運動的刺激下,古本《大學》引起廣泛的關注,發生前述的“《大學》璧回《禮記》”的學術現象,成為乾嘉漢學興起的一條主要線索。李紀祥對此有敏銳的判斷:“返回《禮記》,即宗漢學,宗漢學即宗古本。”基于此,有清一代,雖然今本《大學》依然保持官學地位,但古本《大學》卻成為士子從事學術研究的文本,頗有“科舉法今本,研究宗古本”的分裂之態。實際上這一點,早在明代的湛若水就曾說過:“諸生讀《大學》須讀文公《章句》應試;至于切已用功,更須玩味古本《大學》”,湛氏此言可謂發了清儒的先聲,只是在當時并未形成規模效應。這與同屬四書的《論語》、《孟子》穩居科場和學界頗為不同。縱觀清代代表性學者的《大學》注本,如王夫之、李光地、魏源、惠士奇、毛奇齡、楊亶驊、劉古愚、溫飏、張文檒等皆以遵從古本為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學者在《大學》版本上的唯古本是從的取向。
改本《大學》數量較少
古本《大學》雖年代較之今本《大學》為早,但比較吊詭的現象則是,它引起學界的關注則是在朱子今本《大學》之后。更為準確地說,是到明代中期陽明心學崛起之后,不僅古本《大學》引起重視,同時改動《大學》文本亦迎來推崇和研究的高潮。而至于個中原因則在于,陽明心學對朱子學的沖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朱子學的權威,他們兩者的文本競爭“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即從《大學》文本改訂入手,進行理學學說創新活動。”故在明代陽明心學最為鼎盛的中晚明時期,改本數量最多,可謂冠絕一時。而到清代,“考證之學興起,學者尊注疏、復古本,力主《大學》歸返《禮記》,因之清代雖有改本,已非明季之盛”,主要有胡渭改本、惠士奇改本、甘家斌改本、宗稷辰改本、章鈞改本等八種,可見清代《大學》改本數量遠遠不及明代。
經世致用取向明顯
康有為說:“夫內圣外王,條理畢具,言簡而意賅者,求之孔氏之遺書,其惟《大學》乎?”康氏此言不虛,道出了《大學》所涵具的內圣外王的特質。也正是這一特質,使得《大學》在每逢世道澆漓之際,就會受到格外的重視。就清代而言,明清之際和中晚清的《大學》詮釋其經世致用的詮釋面向最為凸出。如宋翔鳳在詮解《大學》時,“遂釋‘格物’為‘器車’‘河圖’‘膏露’‘醴泉’等物,以傅合《公羊》家著治升平、文成致麟之說”,劉古愚在詮釋《大學》亦有類似做法,在詮釋《大學》“第九章”時道:“生財則須以人力補天地之缺陷,如羲農以至堯舜之所謂則可也。孔子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禮》稱火化之功用,《易》述十卦之制作,子貢欲用桔槔,夫子特短右袂,圣門論財用,未嘗斤斤于理之而不能生之也。今外洋機器,一人常兼數人之功,一日能作數日之事,則真生眾食寡、為疾用舒矣。”眾所周知,孔子并不諱談“財利”,而是主張取之有道,后宋明理學拔高“義”,致使談“利”色變。劉古愚則通過引用孔子的話,來為其“生財”思想進行辯護,他認為儒家對于財力并不單單是理論上的,而是主張生財的,所以西洋的機器皆可引以為用的。可見劉古愚對西方知識、器械并不反對,而是主張變通以為我用。在清代《大學》詮釋史上,如此事例不勝枚舉,他們的詮釋已經不同于其他斷代學者那僅僅關注個人的德性成就,而是轉向到外部經世濟民上來。
要之,經典詮釋既面向過去,亦面對當下,是連接過去與當下的樞紐和津梁。在后經學時代,如何讓古老的經典重新煥發新的經世致用的生命本色,如何防止經典詮釋變成純粹的文獻研究,如何重建我們對經典的信仰,清代的《大學》詮釋的特質無疑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和典范。
- 2022-11-22《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記錄的周人故事
- 2022-11-22說“真淳”
- 2022-11-22平爐臺上的綠豆湯
- 2022-11-22小雪萬物藏 正是積蓄時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