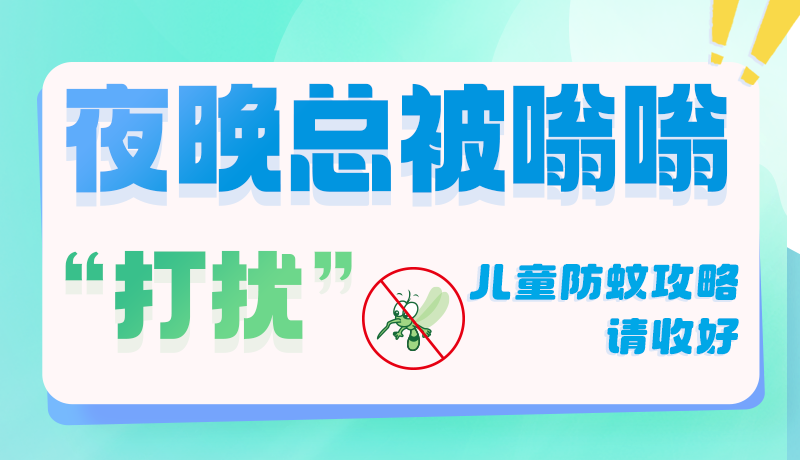華容與水

圖為華容藕池河景色。王綺平攝
記得那年初秋的一個清晨,我們早早出了門。表哥挑著滿滿一擔嫁妝,我跟在后面,和他一樣滿心歡喜。再過兩天,我的鄰居臘姐就會成為他的新娘。
從老家西來河出發,沿逶迤南去的藕池河大堤,一直走到注滋口姑媽家,有好幾十里路。那時我大約五六歲,從未出過遠門,能到繁華的碼頭吃喜宴玩上幾天,自然樂不可支。可誰知,還未到北景港,我就已腿腳酸痛,怎么也不肯邁步了。表哥無計可施,只好停止趕路,讓我把腳泡在江水里。表哥告訴我,這里的水從長江來,一直流到洞庭湖。說來神奇,一股清爽之氣倏然傳遍全身,內心似乎也注入了一股力量。就這樣,我們走一段路,泡一會兒腳,竟在黃昏前趕到了姑媽家。
多年以后,已經長大成人的我,眼前還常常會浮現那一江流水,清洌怡人,神清氣爽。
地處湖南洞庭湖腹地的這片水鄉叫華容。水做的華容,從長江的波瀾壯闊中來,從遠古的飄渺煙雨中來。《九嘆》中屈原放馬洞庭洲灘,登臨墨山,望菱花照影,蘆葦蔥郁,嘆云山蒼蒼,水天茫茫。西漢文學家劉向2000多年前留下的文學影像,與今天的華容及洞庭湖景象,大體上仍然吻合。華容既有大江大湖的滔滔洪流,又有湖港星羅棋布的靈秀。這片土地剛柔并濟,或在盈盈碧波里泛起動人的漣漪,或在澎湃激蕩中獲得磅礴的生機。
倘若你親近了這些水,你就會懂得華容。
生長在水鄉,玩水是天性。炎熱的夏天,走著走著,見到合眼緣的水面,便撲通一跳,扎進水里,那種清涼的感覺實在是叫人痛快。家鄉人大多水性好,小孩子也喜歡泡在小池小塘里撲騰。大家并不講究姿勢,只是比誰游得快、踩水久。待水性長了,再邀三五同伴,去江里湖里游。先拍拍水面,再用水拍拍脖子,最后用水拍拍胸膛,方從容下水。這既是讓游泳者適應水溫,也是提醒自己對水要心存敬畏。
華容人說起話來,也如涓涓清泉,有流水之韻。每當黃昏時分,娘蒸好了熱騰騰的糯香團子,便會站在斜陽里吆喝:“姑兒,伢兒,回來吃飯咧。”華容話的部分發音帶有濃厚的荊楚特色,“聲在湘營音在楚”,保留了古漢語入聲發音短而輕的特點。而語言的傳播與融合,又讓華容話帶有“吳儂軟語”的韻味,說笑間似有水聲鳴響。
一水之隔的湖北小伙兒,若能娶到華容的姑娘,必被鄉親們夸有福氣。常常想起一生愛唱番邦鼓的姨媽。小時候,姨媽喜歡帶我到屋后的清水河洗澡。記得水邊是一簇簇翠綠的野芹菜和蘆蒿,散發著淡淡的清香。三三兩兩的魚兒似乎并不怕人,悠然自得地游來游去,令人忍不住伸手去捉。姨媽一邊給我輕輕搓洗,一邊講著古老的故事,用鄉音古調吟唱:“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我沉浸在那輕柔的音調中,恍惚間覺得自己就是那個頭頂華麗帽纓的翩翩少年,站在孕穗灌漿的稻田里,那一刻,我仿佛聞到了飄在田里的稻花和豌豆花香。
擇水而居的華容人,還以水為師,把“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作為人生哲學,“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寬厚包容而不排外。不少外鄉人遷徙漂泊到華容,尋一處湖洲,搭一個茅棚,就能安穩地扎下根來。對于他們來說,外鄉很快就成為故鄉,他們在華容大地繁衍生息,開枝散葉。聽祖父講,我的先祖就是從江西前溪遷入華容。他們越衡山,漂湘江,過洞庭,一路向北,終于到達向往的魚米之鄉。
自古華容水患不斷,家園一次次被洪水沖毀,但是華容人不服輸,一次次重筑堤壩,重建家園,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集成垸是一個在長江中漂浮千年的小島,有一次我去那里采風,船一靠岸,就看見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獨坐在江邊曬太陽。老人對我們說,兒子在外地安家了,他卻不想住大城市里去,更不愿離開這里。他望著遠處的滔滔江水,語氣十分平靜。
想來,華容人祖祖輩輩生活中的歡欣與痛楚,都因水而生,和水交織在一起,難舍難分。水之于華容,猶如精神血脈般不可分離。
離開華容已多年,可我依然是故鄉那個涉水的孩子。那些水一直滋養著我,我把水做的故鄉帶進了心底。多少次在夢中,欸乃槳聲依舊韻腳清亮。洞庭湖的那一片蔚藍,早已深深地嵌在我心中……(劉創)
- 2021-04-06“梅”好香山
- 2021-04-06劉漢俊:有一個故事,叫長江
- 2021-03-31《花開有聲》:春風化雨 花開有聲
- 2021-03-31寫給天國里的金吉泰老師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微信
中國甘肅網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習強國
學習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