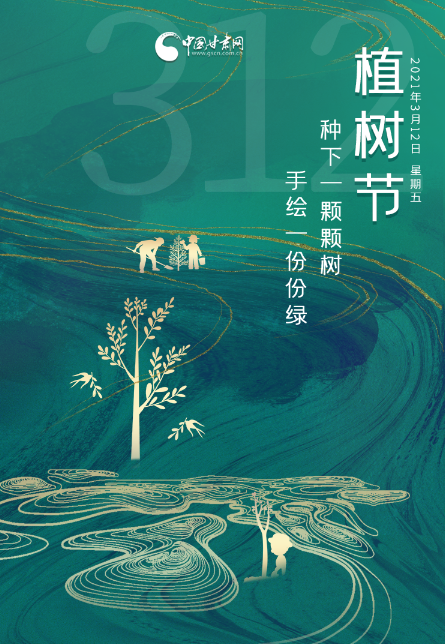《一碗面里的鄉愁》:一場詩意的田野調查
作者:張麗
我很好奇,怎么會有人為一碗面而寫一本書?作家趙瑜在序言里回答了我的疑問,他說寫《一碗面里的鄉愁》是因為偶遇了制作手工空心掛面的非遺傳人,被這充滿審美意味的面條打動了。但讀完這本書,你會發現,它并不是一部簡單的紀實散文。
它寫的不止是一碗面,實際上寫到很多地域文化,寫到地域文化里面那些人的生活狀態。它不僅寫到作家的吃面史,還寫到他的生活史,他的行走史。他試圖通過跟具體的物相關的東西,來反思自己生活的區域,自己走過的地方,以及整個鄉土文化的東西。這么說,似乎讓這本書一下子重了起來,但其實讀起來還是很輕松的。
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是,一個作家做了一場很有詩意的田野調查,然后情思勃發,洋洋灑灑把自己有生以來與面食有關的經歷、感受、想象都梳理一遍,形成了他的面食王國。
趙瑜的“麥收記憶”讓我讀得熱淚盈眶,生于上世紀80年代末的豫南鄉村,磨鐮刀、收割比賽、打場、曬場,繳公糧(我們那兒叫“完糧”),這些莊稼活兒我也一樣經歷過,伴著他的文字,回憶鮮活跳動,身上好像被麥芒和稻穗(我的老家既種麥子又種稻子)扎著似的癢癢……手工農業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作者的記錄竟有了標本的意義。
相信很多人和作者一樣,從農村走向城市,從面(或者米)食走向更廣闊多元的食物,只是沒有作者的才情,能把食物對人的影響形容得如此浪漫。
他說:“十八歲,我到離家一百公里外的小城讀大學。大雪中,在街頭吃了一碗豪放的羊肉湯,遇到一種叫作鍋盔的餅子,像是讀了一部方言完成的小說。”忍不住把這一段劃線,多讀了幾遍,用方言小說來形容地域美食,簡直太貼切了!每到一個新的地方,對人最直接最生猛的觸動就是那入口的食物,地方美食的個性不是每一個外來人都能輕易接納的。很多內地人不能接受海鮮,北方人常常難以理解廣東人對一些野味的鐘情。口味的偏狹有時候是一種自我保護,但相應的,也是一種自我禁錮。
我想起自己在同學的再三慫恿和鼓勵下吃榴蓮的經歷,說實話,如果不是她們“敢不敢咬牙吃三口”的激將,我絕無可能嘗試,但那三口過去,人生的新天地打開了!榴蓮簡直是美食界的最佳偽裝者,它用臭味迷惑了太多膽怯的人,但同時也獎勵了敢于挑戰的人。
就像趙瑜所說,每吃一種食物,都是對人生見識的延伸。
但經歷越豐富,行旅越漫長,離家越遙遠,我們卻越是迷戀手工、匠人這些慢節奏的事物,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史無前例地趨同吧!我們去超市采購一樣的食材,打開手機刷同樣的新聞和視頻,大家一起聊熱點話題,好像一切都可以復制粘貼,周而復始,我們太需要新鮮感和差異化了。
所以,那些跟時間、跟自己較勁的手藝人就成了美好的代名詞,經他們的手,細微的差別也被無限放大。就像做手工空心面一樣,他們隨天氣而動,追逐風和陽光,和面、醒面、切割、盤條……過交、出桿,把面粉變成細如發絲卻中空的面條,這是一場具有審美意味的行為藝術。做面的人付出了時間和心力,吃面的人似乎也感受到了別樣的滋味。
然而這一碗面,并沒有看起來那么輕松美好,尤其是鄉村手藝人,他們的現實生活中充滿了窘迫。做了一輩子空心掛面的張師傅說,他在外面打工,一天可以很輕松地掙200塊錢,有的地方還管吃住,而在家里,做一百斤手工空心掛面,極累,他和妻子兩個人,覺都睡不好,做完一次都要歇息兩三天才能恢復體力,一天也不過是掙兩百元。如果不是因為熱愛,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做的掛面別人覺得好吃,買不到還很失落,這樣一種莫名的“虛榮心”在支撐著,他可能早就放棄了。
我倒覺得支撐張師傅勞累下去的,不是“虛榮心”,而是價值感。他被贊美、被認可、被需要,無論工廠里的機械多么便捷,超市里的面條多么廉價,他都無可取代。這源自唐宋的手藝,傳到了他這里,他便肩負了一種沉甸甸的文化責任。
所以,村子里還是有年輕人選擇了回歸,選擇了繼承傳統,因為“每一次的風不同,面條的味道便不同,每天的溫度不同,做出來的面條的色澤都有細微的變化。”因為那些曾經滋養過我們的美好傳統,生動又唯一。
相關新聞
- 2021-03-12在春天,打開一幅草木與生靈的畫卷——評《詩經動植物圖說》
- 2021-03-10瑰麗的東方世界之旅
- 2021-02-05王光輝:怎樣給孩子們講好敦煌故事——讀趙劍云《敦煌小畫師》有感
- 2021-01-29寫在《故宮營建六百年》出版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