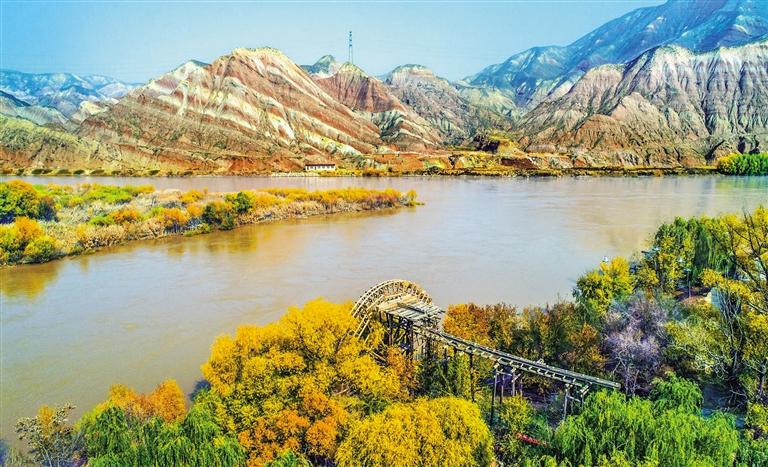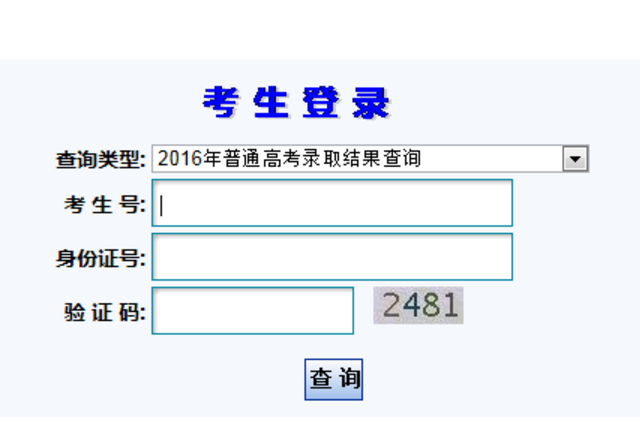作者:岳雯
著名作家劉心武的長篇新作《郵輪碎片》,延續了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主題,即敘寫一代知識分子生命前史與當下生活的交織,叩問著他們的內心秘密和人性真實。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家采用了碎片化的結構形式,以四百個片段的精致跳蕩來呈現四代人的昔日今生,可以視作對接網生代閱讀習慣的嘗試。新穎現代的小說結構與傳統的文學主題將擦出怎樣的火花?讀者如何在郵輪這個有限自足的空間里,感受復雜的現實生活,時代發展的途徑?本版約請青年評論家岳雯專文評述。——編者
有一年,我也參加過郵輪游。裝飾得美輪美奐的郵輪上,各種娛樂設施應有盡有,是一個叫人們流連忘返、放松身心的場所。在甲板,在中庭,在餐廳,我與無數的人擦肩而過,卻并不知曉他們有著怎樣的人生故事。讀劉心武的《郵輪碎片》,那一段已經沉睡的記憶仿佛重新蘇醒過來,那些不知名的路人,也似乎長出了血肉,生成了自己的故事。這或許就是小說的魅力吧。它在喚起我們的日常經驗的同時,也帶領我們打破表象的屏障,深入到人心深處,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習以為常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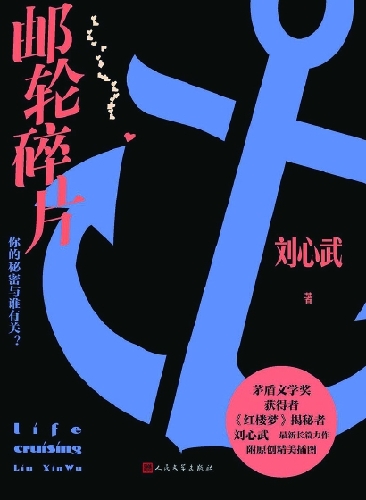
《郵輪碎片》 劉心武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與眾多小說不同的是,這一部長篇小說,竟然是以碎片的形式寫就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小說的形式以突出的方式呈現出來,并塑造了內容本身。劉心武在創作談中回答了為什么要以碎片的形式來寫一個郵輪的故事。他說,“郵輪的空間是有限的,一次郵輪旅游的時間也是有限的,因此,宏大敘事顯然不宜,因要寫實,當然不能采取現代主義的荒誕、變形、錯位,但后現代主義那‘同一空間中不同時間的并列’的拼貼趣味,則大可借鑒,于是,首先確定下來,要拼貼。如何拼貼?想到這幾年接觸到的年輕人,特別是90后、00后,他們有的已經很不適應長篇幅的閱讀,習慣于碎片化的閱讀,特別是在手機上閱讀,手機的屏幕限定了篇幅,故此即使要把豐富的信息傳遞給他們,也必須分割為若干片斷,以碎片方式呈現,如果他們被吸引了,則誘導他們將這些碎片自行拼裝起來,整合為具有廣度與深度的世道人心圖像。”換句話說,這一小說形式,既是由小說的內容決定的,也是根據當下人們的閱讀習慣所作的嘗試。作為讀者的我們,該如何將這447個碎片“拼裝”起來呢?
踏上這場郵輪之旅的,是“中產階層”的一群人。他們中間有退休官員、醫生、作家、大學教授、策劃人等。他們大多在社會轉型時期因為種種機緣,脫離了體力勞動,具備了某種專業技術,并獲得了一定的社會資本和聲望,因而才有能力消費郵輪這一新的旅游產品。作為經歷了不同時期的資深作家,劉心武顯然對這一人群的來歷了然于心。某種意義上,他揭開了這些人物的“前史”。比如,退休官員龍秉謙的人生轉折,竟然憑一張老照片。在母親留下的遺物里,他獨獨看準了母親與一位權貴人物的合影。經由這張老照片開路,經過他巧妙的經營,龍秉謙從工廠調入了機關,并且成為某種級別的官員。在全書中著墨不多的退休醫生,倘若不是因為舅舅的職務之便,又怎么能輕易頂替了旁人,成為省會醫學院的工農兵學員,進而成為醫生,成為一方專家?這些“中產階層”對于自己的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大概是欣欣然的吧。
在這艘郵輪上的游客都是有著良好的經濟條件的,即使是為他們服務的工作人員,住在郵輪的底層,像導游小張、按摩師華瑞生,作家都敘述了他們有著過得去的經濟收入,與游客們并沒有明顯的區隔。全書唯一談得上屬于低收入人群的,是莊有德的司機兼保鏢雷富定。在跟隨“中產階層”工作期間,他耳濡目染了許多他們的趣味,并立志要把兒子培養成進入社會的中游水平。盡管他們的經濟收入已經平穩,但他們的內心還有脆弱時分,有著不安全感的浮現。導游小張一家丟失了手表和金條,盡管懷疑是小時工小樊所為,卻不能有任何作為,別說報案了,倒好像自己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正如老畫家所自省的那樣,因為希望人生的平穩順遂,所以“事事謹慎”。他們有機會看到那兩個叫做明歷與普奔的少年嬉戲,卻發現自己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連交談都是不可能的。小說暗示了不同階層之間的隔膜,在這次郵輪之旅中已然存在。
在這部小說里,劉心武著墨更多的還是知識分子群體。這不僅僅因為作者長期浸潤在文化圈,對此耳熟能詳,寫來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為知識分子畫像,大抵最能傳達作者的文化態度與文學觀念。這個群體中有著怎樣的人物呢?他們有時會情不自禁地夸夸其談,小說的主要敘述者馬自先也忍不住要談歐洲文明,談文藝復興,談什么有愛奧尼亞、多立克、柯林斯柱的古典殿堂,談大圓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在傾聽者仰慕的目光中,他們能獲得自我的存在感。他們精心籌劃、左右逢源,比如策劃人滕亦蘿盡己所能地說服郵輪上的人無償地參與到他號稱的國際性的詩歌評獎活動,是對自己策劃能力的陶醉,也是為了不菲的策劃費。
劉心武在小說中揭示了個別知識分子最大的問題在于善變。像那位叫做宙斯的教授,他聞風而動,甚至不惜將無辜的人作為自己上位的墊腳石,借此將自己利益最大化。在文學上,這個時期他以西方現代派自居;那個時期,他又立刻大加贊美另一種創作手法。就是躺在異國的病床上了,他的那個“巧克力女士”還在心里謀劃著究竟擬一個什么樣的新聞稿給媒體,才能為宙斯和她自己,通過這個突發事件,謀取到最大的利益……可見,宙斯的前后變化,不過是審時度勢,順時勢而為,缺乏知識分子的堅守與良心。讓讀者覺得還不錯的馬自先,在寫作觀念上也是時時刻刻在變,“先嚴格寫實,后浪漫寫實,再全憑想象,又極端到只以形式出新咋呼人,弄過荒誕與魔幻,玩膩意識流和時空錯亂,卻又回歸講故事……”這樣時時刻刻在變的個別作家,意味著缺乏堅實的主體,缺乏自己的根基。這又何嘗不是當下文學創作中存在的弊病。劉心武冷靜地審視著這群知識分子中的個體存在的問題,卻也對他們充滿了同情與憐憫,就連令讀者生厭的宙斯和巧克力女士,如此心機百出,也不過是為了生存,為了活得更好罷了。劉心武說:“所有的生命都不容易,誰都有不能為外人道的隱秘。”但文化人還是要保持中正大氣,保持積極有為,盡管做到并不容易。
在小說的結尾,為了給父親報仇揍了宙斯的郝向陽陷入到復雜的情緒中,他說:“這一切,究竟都是為什么?誰讓他,誰讓我,還有好多別的人,成了現在這個樣子?”這似乎可以看作是這部小說的緣起。《郵輪碎片》在美學精神上受到《紅樓夢》的影響,有輕松、幽默的韻致,也不乏諷刺的筆法寫一次郵輪之旅,小說是對上個世紀70年代至當下的社會生活進行嚴肅的省思。它舉重若輕,打開了人性的扇面,也照亮了我們的來路。它看似是零碎的,像五彩斑斕的萬花筒,卻構成了立體的社會圖景,并具有了歷史的縱深感。從這個意義上說,《郵輪碎片》是以最具時代感的形式超越時代本身的重要嘗試。
(作者為青年文藝評論家、中國作協創研部副研究員)
相關新聞
- 2017-01-20隴周刊(2017年 第3期)
- 2017-01-26隴周刊(2017年 第4期)
- 2017-02-10 隴周刊(2017年 第5期)
- 2017-02-17 隴周刊(2017年 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