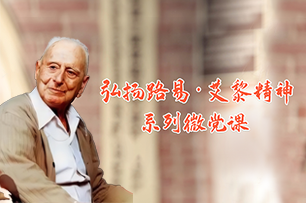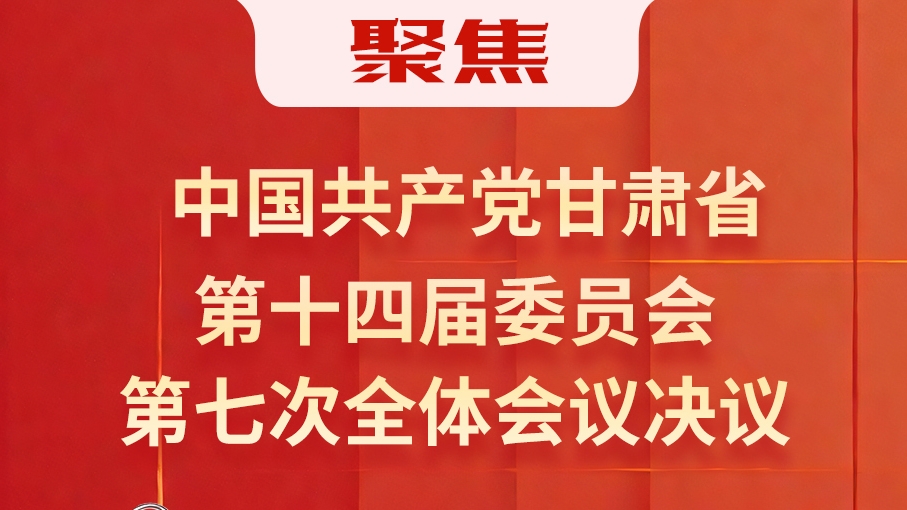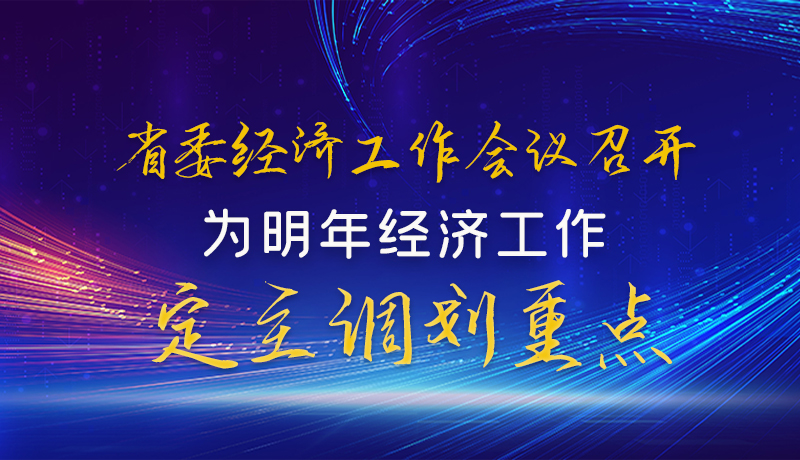原標題:作家在線||人物風(fēng)采:救死扶傷的隴上天使/姬廣武
姬廣武,祖籍甘肅臨洮,生長于甘肅武威。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甘肅省政府文史研究館研究員、金城文化名家,蘭州市作家協(xié)會第四、五屆副主席。歷任蘭州市委組織部黨員管理處處長、蘭州市委巡察辦副主任等職。出版報告文學(xué)《百萬移民》《世紀決戰(zhàn):中國西部農(nóng)村反貧困紀實》(上、下卷)《歷史深處:“6·26”醫(yī)療隊在隴原》及長篇小說《貨郎客》(合著)等10余部。代表作《世紀決戰(zhàn)》獲第十二屆中國人口文化獎報告文學(xué)類作品金獎、甘肅省首屆黃河文學(xué)獎一等獎、蘭州市第五屆金城文藝獎一等獎。曾被評選為甘肅省文聯(lián)第二屆“徳藝雙馨”文藝家,蘭州市第四批、第五批專業(yè)技術(shù)拔尖人才。

救死扶傷的隴上天使
——“6·26”醫(yī)療隊在甘肅
姬廣武/文
2012年1月11日晚,“感動甘肅·2011十大隴人驕子”頒獎晚會在甘肅大劇院隆重舉行,“6·26”甘肅醫(yī)療隊榮膺“感動甘肅·2011十大隴人驕子”特別獎。
組委會給“6·26”甘肅醫(yī)療隊的頒獎詞是:十分熟悉的職業(yè)與漸漸陌生的“6·26”,把難忘的一段美好重現(xiàn)在我們面前,他們來自祖國的四面八方,卻把青春獻給了甘肅,救死扶傷讓他們成為隴上天使,普及預(yù)防科學(xué)把他們鑄成一組群雕,成為山鄉(xiāng)接近文明的一道風(fēng)景。
歲月如歌。回眸50多年前,一大批來自北京等大城市的“6·26”醫(yī)務(wù)工作者,以血汗鑄就了甘肅衛(wèi)生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豐碑。他們的精神、他們的事業(yè),永遠留在了這里。“6·26”醫(yī)務(wù)工作者的優(yōu)良醫(yī)德和精湛醫(yī)術(shù),在甘肅的土地上生根發(fā)芽,代代相傳。歷史不會忘記,甘肅人民永遠懷念他們、感激他們。甘肅的高山,鐫刻著他們的事跡,甘肅的大地,永遠流傳著他們的故事!
舉家告別北京,隴原矗起豐碑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主席在批評衛(wèi)生部是城市“老爺衛(wèi)生部”的同時,發(fā)出了“把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nóng)村去”的偉大指示,史稱“6·26指示”。這是毛主席對衛(wèi)生工作一貫的指導(dǎo)思想,也顯示了毛主席安邦治國的戰(zhàn)略思想。
“6·26”指示發(fā)出后,一個“到農(nóng)村去,為五億農(nóng)民服務(wù)”的熱潮,從首都北京,從全國各大城市,迅速向農(nóng)村、牧區(qū)、邊疆涌動。在較短時間內(nèi),衛(wèi)生部從中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北京醫(yī)學(xué)院系統(tǒng)、北京市各級醫(yī)院選派了2000多名醫(yī)務(wù)工作者到甘肅安家落戶,為農(nóng)民群眾防病治病;同時,一大批醫(yī)學(xué)院校畢業(yè)生志愿來到甘肅參加工作;從1967年開始,衛(wèi)生部每年還選派400人的巡回醫(yī)療隊赴甘肅河西走廊開展公共衛(wèi)生和醫(yī)療服務(wù),歷時10年。與此同時,解放軍駐甘部隊各醫(yī)院積極支持地方衛(wèi)生事業(yè),選派了大批醫(yī)務(wù)人員深入農(nóng)村;全省各城市醫(yī)務(wù)人員,也懷抱理想,奔赴邊疆、農(nóng)村和牧區(qū),人們親切地稱呼他們?yōu)?ldquo;6·26”醫(yī)療隊。
“6·26”指示發(fā)表后,北京市很多醫(yī)院敲鑼打鼓地去衛(wèi)生局請戰(zhàn),主動要求支援大西北。1965年,北京平安醫(yī)院支援酒泉鋼鐵公司建設(shè),約200名醫(yī)護人員整體搬遷嘉峪關(guān),首開北京醫(yī)院遷往甘肅之先河。北京天壇醫(yī)院也整體搬遷甘肅,全院500多人,分別在慶陽、天水、臨夏組建多家醫(yī)院,開始了他們在隴原的十年奉獻之路。就這樣,一些醫(yī)院被整體搬遷,一些醫(yī)院部分搬遷,僅北京醫(yī)學(xué)院,就有三分之一的人下了甘肅。他們當(dāng)中,有鬢發(fā)斑白的老教授、老醫(yī)生,也有參加工作不久的年輕醫(yī)生……
來自北京的大批醫(yī)務(wù)人員幾乎都是舉家赴甘。北京車站,西行的列車即將啟動,激昂的誓言與飄灑的淚花同在。天壇醫(yī)院曲敬新總護士長奔赴甘肅,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壓力:母親因病癱瘓在床,怎么辦?曲敬新著急、難過地哭過好多次。但她還是找到組織,報上了名,表示要堅決聽黨的話,支援甘肅社會主義建設(shè)。就這樣,曲敬新和愛人一副擔(dān)架,將母親抬上了開往甘肅的列車。這一去,就是50多年。她在“羲皇故里”扎下根來,為當(dāng)?shù)厝罕姷慕】捣?wù)了一輩子。
景翙筑,河西堡北京醫(yī)院婦產(chǎn)科主任,1969年隨北京市第一醫(yī)院搬遷河西堡。陪伴她來到這片戈壁灘上安家落戶的,是時為北京市航空學(xué)校教師的愛人陳幼孚和11歲的獨生子。陳幼孚是1953年畢業(yè)于清華大學(xué)航空系發(fā)動機專業(yè)的高材生,隨遷來到河西堡后,在武威地區(qū)運輸公司三車隊“做技術(shù)革新工作,什么都干”。在這里,他們一家度過了12年的難忘歲月……政策規(guī)定,下放人員家屬隨遷,戶口遷出,住房上交,故僅河西堡醫(yī)院隨遷家屬中,有中國人民大學(xué)、中央民族學(xué)院、北京鋼鐵學(xué)院的教師和北京市文藝團體的美工、音樂等專業(yè)人員,以及北京制藥廠的技術(shù)人員和北京機床廠的工程師、技術(shù)員等。許許多多醫(yī)務(wù)人員的配偶在其他領(lǐng)域,也為甘肅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事業(yè)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據(jù)統(tǒng)計,遷甘醫(yī)院、衛(wèi)校計有34家,其中:100張床位的醫(yī)院3所,80張床位的醫(yī)院1所,50張床位的醫(yī)院7所,30張床位的醫(yī)院20所,20張床位的醫(yī)院1所,衛(wèi)(護)校2所。“戰(zhàn)斗在全省52個點上。”約占當(dāng)時全省衛(wèi)生技術(shù)人員十分之一的大批北京醫(yī)務(wù)人員到來后,積極開展巡回醫(yī)療、幫助培訓(xùn)赤腳醫(yī)生、建立合作醫(yī)療、開展愛國衛(wèi)生運動,拯救了無數(shù)農(nóng)民寶貴的生命,保護了他們的健康,促進了當(dāng)?shù)剞r(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所到邊遠農(nóng)村、牧區(qū)的醫(yī)療衛(wèi)生面貌開始發(fā)生深刻的變化。甘肅省省級醫(yī)院的醫(yī)療水平,七八十年代在全國也都處于比較高的水平,因為各大醫(yī)院都有一批從北京下放來的醫(yī)生和科主任,他們當(dāng)時就已是知名的專家。
1970年2月,擁有200張病床,350多名醫(yī)護人員的北京市第一醫(yī)院一分為二,下放到了甘肅省。該院外科骨干力量主要來到新的工礦區(qū)永昌縣河西堡鎮(zhèn),內(nèi)科骨干力量多去了永登縣。河西堡北京醫(yī)院幾經(jīng)演變,成為今天的金昌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其名稱雖然幾經(jīng)變化,但是,永遠不變的,是當(dāng)?shù)馗刹咳罕妼λ顡吹母星楹蜔o限的懷念。今天,許多當(dāng)?shù)乩习傩杖匀涣?xí)慣而親切地稱其為“北京醫(yī)院”。
1978年4月,甘肅中醫(yī)學(xué)院(現(xiàn)甘肅中醫(yī)藥大學(xué))正式成立。重師興教,人才是關(guān)鍵。省委、省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大批在甘的北京醫(yī)務(wù)人員,他們中間,有許多學(xué)貫中西,具有高級職稱的專家教授。就這樣,以來自北京中醫(yī)學(xué)院(現(xiàn)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為主的一批中年知識分子,被選調(diào)到學(xué)院任教。1980年,通過全省統(tǒng)考,又從這批人員中選拔了一批優(yōu)秀人才,張世卿成長為甘肅中醫(yī)學(xué)院院長。這兩次高精尖人才的引進,極大充實和加強了中醫(yī)學(xué)院的師資隊伍。他們既有扎實深厚的醫(yī)學(xué)理論知識,又有多年農(nóng)村基層工作的豐富臨床診療經(jīng)驗,人員占到學(xué)院建院之初教師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達40多名,成為甘肅中醫(yī)學(xué)院教學(xué)工作和學(xué)科建設(shè)的奠基人,支撐起了甘肅中醫(yī)藥高等教育事業(yè)的擎天大廈。
酒泉鋼鐵公司醫(yī)院、天水地區(qū)第一人民醫(yī)院、慶陽地區(qū)第二人民醫(yī)院、平?jīng)龅貐^(qū)第二人民醫(yī)院、甘肅省腫瘤研究所、甘肅省衛(wèi)生防疫站、甘肅中醫(yī)學(xué)院、隴西縣6·26醫(yī)院、民勤縣西渠公社6·26醫(yī)院……這些由“6·26”醫(yī)務(wù)工作者建立起來的醫(yī)院和大學(xué),如同一座座不朽的豐碑,永遠矗立于隴原大地,從根本上改變了甘肅醫(yī)療人才匱乏、農(nóng)村缺醫(yī)少藥的面貌。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1980年前后,因為落實政策、工作需要、家庭困難等種種原因,一些“6·26”醫(yī)務(wù)人員又回到了北京,一些醫(yī)院遷回原址。但是,他們帶出了學(xué)生,培養(yǎng)了隊伍,他們以自己高尚的醫(yī)德和救死扶傷的精神,影響、教育和感染了幾代隴原人民。他們默默的付出,一如閃爍的繁星雖無名,卻照亮了整個夜空,譜寫了甘肅衛(wèi)生史上最光輝的一頁。
劉宏、任華明夫婦1967年畢業(yè)于中國醫(yī)科大學(xué)8年制醫(yī)療專業(yè),來到甘肅,他們給人事部門說的第一句話是: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就這樣,他們“一竿子插到底”,來到渭源縣慶坪公社中心衛(wèi)生院安家落戶。在這個遠離縣城30多公里,進一趟城步行需要4、5個小時,山大溝深,被稱做“干北山”的地方,整整度過了7個年頭,他們的獨生子也降臨在這個窮苦的山鄉(xiāng)。劉宏來到慶坪后,即擔(dān)任衛(wèi)生院院長。他注重傳、幫、帶,培養(yǎng)當(dāng)?shù)蒯t(yī)務(wù)人員。主動開展婦、兒、內(nèi)、外科等各項治療和手術(shù),吸引了周邊4個公社的患者前來就醫(yī),遇上無錢看病買藥的患者,又總會毫不猶豫地拿出自己的工資為他們墊付醫(yī)藥費。劉宏、任華明的童年是在“延安保育院小學(xué)”度過的。任華明的叔父是老一輩革命家任弼時的堂兄,母親丁祝華是中共早期黨員,劉宏的父親劉道安是黨的“七大”代表。他們扎根甘肅農(nóng)村,默默服務(wù)農(nóng)民群眾,其精神動力在哪里?他們究竟在追求什么?劉宏擲地有聲地對我說:“從小就受黨的教育,就是為人民服務(wù)。什么地方有人民需要,我們就去。我們是自愿去的,就是打算在農(nóng)村干一輩子!因為我們是老共產(chǎn)黨員的后代……”
毛江森,中國科學(xué)院院士、浙江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原院長、甲型肝炎活性疫苗研發(fā)者。1969年,毛江森和夫人張淑雅從中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下放甘肅,在武都縣岸門口公社衛(wèi)生院和甘肅省衛(wèi)生防疫站工作了8年。1972年,隴西縣出現(xiàn)疑似“出血熱”疫情,很多嬰幼兒失去生命,全縣陷入恐慌之中。毛江森受命前往調(diào)查,他憑著多年從事病毒研究的扎實理論功底和實踐經(jīng)驗以及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結(jié)果,力排眾議,作出了這是因成人食用發(fā)霉糧食,毒素經(jīng)母乳引起嬰幼兒內(nèi)出血疾病的大膽推斷。唯一的選擇,是馬上停止發(fā)放救濟糧!可是,調(diào)查結(jié)果沒有實驗室數(shù)據(jù)的支持,萬一推斷有誤,后果不堪設(shè)想。停發(fā)救濟糧,在當(dāng)時的背景下,要承擔(dān)很大的政治責(zé)任,但死亡在不斷增加,時間不等人。毛江森毅然將結(jié)果逐級上報。他的建議,得到了時任縣革委會主要領(lǐng)導(dǎo)的大力支持。救濟糧停發(fā)幾天后,因病致死的嬰幼兒明顯減少。后來,蘭州大學(xué)生物實驗室從這批從東北運來,風(fēng)吹雨淋十多天發(fā)霉的救濟糧里分離出了毒素,證明該毒素能破壞人體凝血機制。在這次事件中,毛江森以科學(xué)的態(tài)度、知識分子的良知、醫(yī)生的責(zé)任和對道德與真理的追求斗膽上書,從而避免了更多悲劇的發(fā)生。
上世紀90年代全國聞名的“科技首富”遲斌元,曾是一位河西堡“北京醫(yī)院”的醫(yī)務(wù)人員,來甘前后一直遭受政治上的不公待遇。調(diào)至蘭醫(yī)二院工作后,他致力于從豬血中提煉速效止血藥“凝血酶”的研究,并取得成功。但遺憾的是這一首創(chuàng)性的成果一直未能走出實驗室。在過去的半個世紀時間里,世界上只有英、美、日等少數(shù)國家能人工提取生產(chǎn)凝血酶,但價格昂貴,這種速效止血藥我國過去只能依賴進口。西方是從人血、牛血中提取,而遲斌元是從來源更豐富更便宜的豬血中提取。后來,他到北京工作。1987年,在中國科協(xié)的牽線下,遲斌元和妻子司華帶著他們的科研成果,從北京輾轉(zhuǎn)到珠海,找到投資方,建立了總工程師負責(zé)制的珠海生化制藥廠,生產(chǎn)凝血酶凍干劑。在很短的時間里,把一個投資420萬元的企業(yè)發(fā)展為擁有7000多萬元固定資產(chǎn)的全國明星企業(yè)。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老人家視察珠海的第一站,就是遲斌元一手創(chuàng)辦的珠海生化制藥廠。當(dāng)聽遲斌元匯報公司主打產(chǎn)品凝血酶已成功地打入了國際市場時,鄧小平大加贊賞,說:“我們應(yīng)該有自己的拳頭產(chǎn)品,創(chuàng)造出我們國家自己的名牌,否則就會受人欺負。這就要靠我們的科技工作者出把力,擺脫受人欺負的局面。”也是這一年,珠海市制定了“科技重獎”的政策,遲斌元是那一年的特等獎獲得者。一輛奧迪轎車、一套公寓和一張287184元的支票,讓他成為“科技百萬富翁”,獎金數(shù)額接近諾貝爾獎,由此,開創(chuàng)了中國知識分子獲獎金額的最高紀錄。
夏恩蘭,中國婦科內(nèi)鏡醫(yī)學(xué)——宮腔鏡診治醫(yī)學(xué)的奠基人與開拓者。1970年1月,夏恩蘭所在的北京月壇產(chǎn)院整體下放到甘肅靖遠礦區(qū)。在甘肅的10年中,有一個現(xiàn)象深深刺痛著夏恩蘭的心。在當(dāng)?shù)氐娘L(fēng)俗習(xí)慣中,女性不能沒有子宮,一個女人一旦因為患病摘除了子宮就被視為沒有了性別,不男不女,貓狗不如。作為婦產(chǎn)科醫(yī)生,夏恩蘭常常眼看著子宮出血已經(jīng)威脅到病人的生命了,卻不能實施子宮切除手術(shù)。1989年12月,她從一本英文醫(yī)學(xué)期刊上看到了一篇介紹宮腔鏡診療技術(shù)的文章,在操作方法、治療原理方面,竟和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這是一項集光、電、超聲、顯像、視頻技術(shù)和診療為一體的醫(yī)療技術(shù),而當(dāng)時這篇文獻并沒有引起我國婦產(chǎn)科醫(yī)學(xué)界的普遍關(guān)注。但是,夏恩蘭卻從中洞悉到婦科醫(yī)療革命性的時代即將到來。半年后,由她開創(chuàng)的中國宮腔鏡電切技術(shù),被永遠地載入中國婦產(chǎn)科臨床醫(yī)學(xué)的史冊,成為婦科醫(yī)療技術(shù)革命的里程碑,被人們尊為“中國宮腔鏡之母”。
1967年夏天,馬明良從6年制的北京中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了。9-12月,他踴躍報名,參加衛(wèi)生部第二批赴甘肅河西走廊巡回醫(yī)療隊,在山丹縣霍城、軍馬場工作。翌年8月,他畢業(yè)分配,來到干旱、貧困的渭源縣。那一天陰雨連綿,縣城街道非常泥濘,離開北京時穿著短袖,到了當(dāng)?shù)兀呀?jīng)該穿絨衣了,但衣服都打在行李中,十分寒冷。在純山區(qū)的秦祁公社,他看到,當(dāng)?shù)氐睦先擞械倪€盤著清代的大辮子,農(nóng)民群眾生活非常艱辛,又非常純樸。交公購糧時,老鄉(xiāng)們晚上不睡覺,把地里的那點最好的糧食連夜用連枷打好,送到糧站。他被渭源農(nóng)民的純樸深深感動著,為了少花錢,治好農(nóng)民的病,馬明良發(fā)揮中醫(yī)藥簡、便、效、廉的特點,設(shè)計出一些簡便方。他與慶坪衛(wèi)生院的甘肅臨洮籍中醫(yī)靳鳳英喜結(jié)連理,組成了幸福家庭。從此,他成了地地道道的甘肅女婿,不但渭源話說的流利,還學(xué)會了喝罐罐茶。“入鄉(xiāng)隨俗,少放點茶葉煮煮,就跟人家能拉上話了。”他風(fēng)趣地說。馬明良1990年回京,執(zhí)教于北京中醫(yī)藥大學(xué)。立德、立功、立言,乃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三立完人”的準則;“非仁愛之士不可托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則是古代醫(yī)生的行為規(guī)范。無論是作為教師還是作為醫(yī)生,馬明良都上不愧天,下不愧地,因為他做的很好。
在“千年藥材之鄉(xiāng)”定西,中國工程院院士孫燕的名字為許多人所熟知,這是因為他和一個富民產(chǎn)業(yè)聯(lián)在一起。1970年,孫燕帶著妻兒,從北京來到定西地區(qū)醫(yī)院安家落戶,這里盛產(chǎn)的黃芪、黨參深深吸引著他的目光。回京后,他開展了“扶正中藥促進病人免疫功能”的課題研究,研制出了貞芪扶正沖劑、膠囊,扶正女貞素和固元顆粒等中藥制劑,獲得四項專利。如今貞芪扶正膠囊和顆粒被列入國家基本藥品目錄,進一步帶動了定西中草藥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對定西農(nóng)民脫貧增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關(guān)碧琰,兒科著名專家,她對甘肅有著深厚的故鄉(xiāng)情結(jié)。她回憶說:“在甘肅成縣的時候,我是兒科大夫,當(dāng)?shù)貎和瘋魅静√貏e多,當(dāng)時工作真累,但是覺得很痛快!”關(guān)碧琰用這樣一句話來總結(ji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關(guān)碧琰在臨床醫(yī)療十分繁忙的情況下傾自己所學(xué),堅持開展兒科診療護理培訓(xùn)工作,為當(dāng)?shù)嘏囵B(yǎng)出了一批兒科醫(yī)護專業(yè)人員。她還幫助地方醫(yī)院訂立診療常規(guī),完善各項制度。從北京醫(yī)學(xué)院下放來到成縣的丈夫吳建中工作也十分突出,是新中國成立后培養(yǎng)的第二批研究生。關(guān)碧琰意味深長地說,“回想起成縣的十年啊,確實是難忘的十年,我覺得也挺值得的。有一次,成功救治了一位患兒,中午我聽見宿舍門口有響動,開門一看,門口放了一堆老玉米,遠遠的就看見一個老農(nóng)背著一個背簍離去了。我會永遠記著這個鏡頭,甘肅人民的純樸、善良,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成為一生中不可磨滅的記憶,甘肅永遠是我們的家……”
責(zé)任高于一切,榮譽高于一切,成就高于一切。1980年6月,王永祿離開播撒了11年血汗和淚水的甘肅宕昌,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回來一無所有,家具20元處理了。下放十年,得了十年的紙回來。”——離開宕昌時,王永祿丟棄了很多東西,唯獨帶回了成摞的獎狀和榮譽證書。這是當(dāng)?shù)卣腿嗣駥Ρ本┽t(yī)務(wù)工作者的最高褒獎。他斬釘截鐵地說:“什么東西都可以扔,都可以不帶,唯獨這獎狀我一定要背回去!”
難忘美好記憶,故鄉(xiāng)情結(jié)永存
2021年2月4日,為榆中老百姓服務(wù)了13年的北京市第一傳染病醫(yī)院高崖醫(yī)療隊帶隊領(lǐng)導(dǎo)吳永勝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臨終前,他囑咐兒子吳志強,一定要將自己的一部分骨灰撒在榆中縣。去世后,他依然愿意回到他魂牽夢繞的榆中大地,這是一種怎樣的情懷,其中蘊含著多少懷念和不舍?2021年3月27日,吳永勝落葉歸根,回歸第二故鄉(xiāng),長眠在縣第一人民醫(yī)院的一顆松柏樹下……
許多“6·26”醫(yī)務(wù)工作者畢生獻身隴原,為甘肅人民的健康和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們的業(yè)績璀璨奪目、事跡蕩氣回腸、精神高山仰止。
甘肅省人民醫(yī)院專家影像張書盛、孟憲慎畢業(yè)于中國醫(yī)科大學(xué),相同的理想和信念使兩人組建了幸福的家庭,并走上了服務(wù)甘肅人民的人生之旅,50多年矢志不渝。他們說,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是組織的信任、甘肅人民的關(guān)愛,還有家人的理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北京的一些大醫(yī)院邀請他們回去,但一次次都是因為組織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讓他們選擇留在了這里,成了永遠的大西北人。在孟憲慎的努力下,省人民醫(yī)院“乳腺病診斷中心”正式組建起來了。孟憲慎是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省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張書盛享受國務(wù)院特殊津貼。這些榮譽是甘肅人民對他們獻身隴原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最好褒揚。
“甘肅變成了家,北京變成了老家。”這是蘭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原院長李其棠的人生寫照。從大學(xué)畢業(yè)來到甘肅至今的50多年間,他記不清看過多少病人,做過多少手術(shù),可他沒有給自己的父母、親人看過一次病,也沒有帶他們?nèi)ミ^醫(yī)院。讓李其棠一輩子都揪心的是:“父母走的時候,我都不在身邊。父親生病住院后,我去北京看望,第二天,看到父親病情有所好轉(zhuǎn),我又急匆匆的趕回蘭州,原因是有幾臺手術(shù)已經(jīng)因此而延期。回來的第三天,父親就去世了。我非常內(nèi)疚,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原諒自己。我的母親走得很突然,她老人家去世以后,我流了一夜眼淚。沒有給父母看過一次病,沒有盡到一個兒子的孝心,這是我最大的遺憾。忠孝難兩全啊!”50多年的無私奉獻,李其棠無怨無悔。他說“甘肅就是我的故鄉(xiāng),我愿意把自己的余生獻給需要的病人,獻給甘肅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
從北京到黨原鎮(zhèn)的路,王富慶已經(jīng)不知道走過多少回。1969年11月,北京醫(yī)學(xué)院人民醫(yī)院的滿族醫(yī)生王富慶和夫人霍瑞莘,帶著母親、岳母和一雙年幼的兒女,3代6口人,輾轉(zhuǎn)千里來到平?jīng)龅貐^(qū)涇川縣黨原鎮(zhèn),住在一間小屋里,演繹了30年的苦樂人生,真正為農(nóng)民群眾看了一輩子病。2005年,孝順的女兒把退休在家的王富慶老兩口接回了北京,可是每年夏天,他們都會回黨原住一段日子,覺得到了那兒就特別親切。“我們很舍不得這個家!”聽到他回來,很多鄉(xiāng)親們都會找上門來,請他再給自己看回病。
何可英,副主任護師,一位曾擔(dān)任周恩來總理保健護士19年之久的省人民醫(yī)院離休干部,周總理和鄧大姐贈給她的紀念冊是她永遠的光榮與自豪。1969年,何可英自愿報名,與愛人王醒和兩個孩子來到甘肅靖遠安家落戶。她說:“中國人,只要是為祖國、為人民,在哪里工作都一樣,哪里的黃土不埋人啊”。樸實的語言,擲地有聲,坦蕩的胸襟,令人敬仰。
采得百花成蜜后,化作春泥更護花。金文媺,甘肅省中醫(yī)院兒科原主任,黨的十三大代表、中國婦女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先后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等光榮稱號。她的愛人夏永潮也以其在中醫(yī)理論和臨床上的卓越貢獻,被甘肅省人民政府授予首批“甘肅省名中醫(yī)”榮譽稱號。為了在臨床上找到效果好、副作用少的藥物治療小兒疾病,突出中醫(yī)特色,金文媺鉆研中醫(yī)古典書籍,研發(fā)中藥靜脈注射藥物,并在每種新藥使用之前,都要在自己身上先做試驗,親自滴注新藥配制的液體,感受藥物的反應(yīng),在確定沒有副作用后,才應(yīng)用于病兒。1997年8月2日,金文媺因突發(fā)腦溢血去世,年僅61歲,忠骨埋隴原。
感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他們的事跡之所以感人,是因為他們在激情燃燒的歲月里,在自己最美好的年華里,無怨無悔的響應(yīng)祖國召喚,奔赴甘肅農(nóng)村貧困地區(qū)開展醫(yī)療衛(wèi)生服務(wù),為解除群眾疾苦、培養(yǎng)衛(wèi)生技術(shù)人才、把滿足基層群眾對醫(yī)療服務(wù)的需要,當(dāng)作自己義不容辭的人生追求。
發(fā)揚優(yōu)良傳統(tǒng),譜寫歷史新篇
2018年8月,年近八旬的北京公安醫(yī)院主任醫(yī)師王久成與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生物系的夫人孟培麗又一次不辭辛勞、風(fēng)塵仆仆重返陜甘寧革命老區(qū)環(huán)縣,“重溫‘6·26’指示,再為鄉(xiāng)親出趟診”。他是已知唯一一名既參加了衛(wèi)生部第一批和最后一批赴河西走廊醫(yī)療隊,同時又是在甘肅工作10年的北京醫(yī)務(wù)人員。他把心留在了甘肅,留在了環(huán)縣,幾十年來,一直關(guān)心環(huán)縣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在毛井鄉(xiāng)衛(wèi)生院,他講傳統(tǒng),診病人,鼓勵新一代醫(yī)務(wù)工作者,要永遠把患者放在第一,要永無止境學(xué)醫(yī)術(shù)……
毛主席的“6·26”指示和北京等城市大批醫(yī)務(wù)人員的到來,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精神和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經(jīng)過50多年歷史風(fēng)云的淬煉,依然歷久彌新。在甘肅貧瘠的土地上,在長達數(shù)十年的時間里,他們?yōu)槲覀儙砹宋拿鞯哪_步和先進的文化。甘肅是“6·26”指示的受益者,沒有“6·26”指示的貫徹落實,甘肅衛(wèi)生還將在更加困難的環(huán)境中前行。“6·26”醫(yī)療隊的到來,使甘肅在極度缺醫(yī)少藥的情況下,如久旱遇甘霖,對于緩解群眾看病難、提高基層醫(yī)療技術(shù)水平,同時也為甘肅的醫(yī)療新技術(shù)開創(chuàng)和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深刻的政治、歷史意義。他們不僅帶來了精湛的醫(yī)技,而且?guī)砹肆己冕t(yī)風(fēng),全省醫(yī)務(wù)工作者向“6·26”醫(yī)務(wù)工作者學(xué)習(xí),大力發(fā)揚他們的無私奉獻精神,面貌蔚然一新,醫(yī)德醫(yī)風(fēng)交口稱贊。
“6·26”指示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chǎn)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的崇高宗旨,“6·26”醫(yī)務(wù)工作者“對黨忠誠、熱愛人民、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精神是留給甘肅的寶貴精神財富,在甘肅這片熱土,“6·26”精神和甘肅精神水乳相融,鑄就了甘肅醫(yī)務(wù)工作者獨特精神內(nèi)涵,成為甘肅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時代,我們要學(xué)習(xí)“6·26”醫(yī)務(wù)工作者的好傳統(tǒng)、好作風(fēng),把他們樹立的大旗扛起來,把他們的精神傳承下去,發(fā)揚光大。在抗擊新冠疫情的特殊時期,特別要發(fā)揚和傳承老一輩醫(yī)務(wù)工作者的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著力加強鄉(xiāng)村醫(yī)療建設(shè),助推鄉(xiāng)村振興,建設(shè)健康甘肅,為提高人民群眾的健康水平做出新貢獻,扎實推進甘肅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要大力弘揚“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肅精神,以十倍之努力,百倍之干勁,匯聚起加快建設(shè)幸福美好新甘肅、不斷開創(chuàng)富民興隴新局面的磅礴力量。
“6·26”醫(yī)務(wù)工作者的歷史功績,甘肅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注:原載《人文甘肅》第十輯
來源:飛天文藝
- 2024-12-13《禹王書》:玉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
- 2024-12-13【甘快看】常沙娜:將敦煌藝術(shù)融入生命,將有限生命投入無限創(chuàng)作
- 2024-12-121984年路易·艾黎等八人在山丹縣招待所合影 中國日報社記者攝影
- 2024-12-10人物春秋 |《儺神賦》——記非遺儺面?zhèn)鞒兄驹刚唏R正德先生印象

 西北角
西北角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中國甘肅網(wǎng)微信 微博甘肅
微博甘肅 學(xué)習(xí)強國
學(xué)習(xí)強國 今日頭條號
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