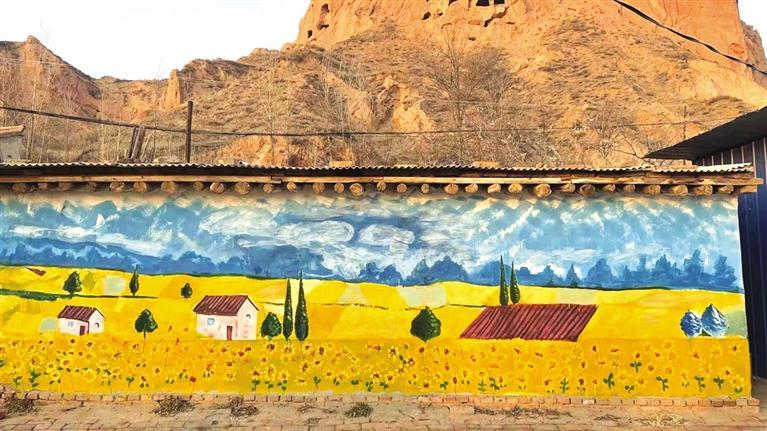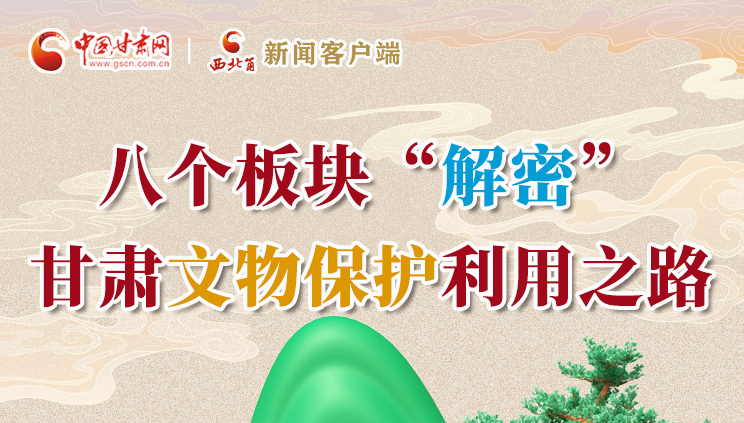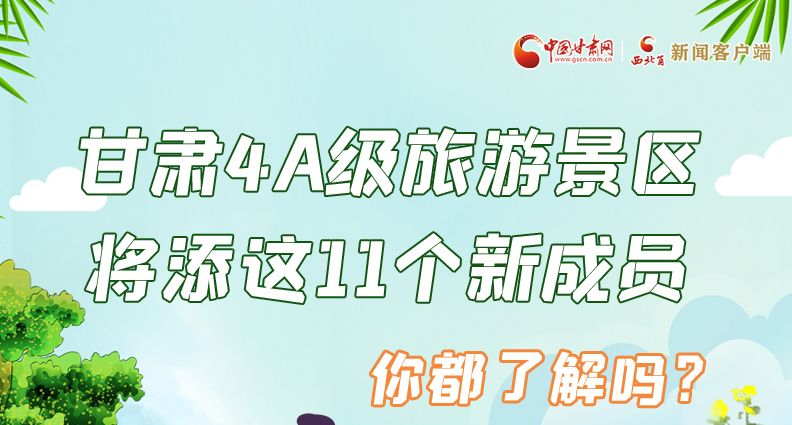□ 劉建寬
風 物 志
“耕讀第”是三陽川農耕文明的進步。川道人家無論窮富、能耐大小,古今盛行門窩刻有“耕讀第”三個大字,其光照生輝,凸顯大門的視覺美感。有些人家還信仰人、財都出在門里,立門時講究放入筆墨紙硯,企盼出個讀書人。川里有些百年以上的門窩“耕讀第”常見顏柳歐趙的楷書,肥潤開闊。近現代的大多是翁劉成鐵、王了望、尤愛的行楷,以示祖德清明,家風雅正。廳房中再掛上朱柏廬的治家格言,教訓兒女們忠誠孝子、讀書耕田。這些是三陽川農戶人家,一代代的傳達和滲透。
在三陽川定義“耕讀第”較為寬泛,說大了是發展方式和精神價值;說實了是耕織傳家、經書濟世。但川里人把“耕讀第”的蘊涵百年來又延伸了,漸漸地演變成父輩俯首甘為勞累耕織,供給娃娃念書;后輩卻矢志不渝,發憤苦讀,想把窮根拔掉。慢慢地“耕讀第”成為長輩和晚輩間無聲的契合,也是無聲的訓導。
“耕讀第”在三陽川祖輩們心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總覺得有耕有讀才能光耀門楣,是過好日子的兆頭。就像我太爺,是位地道的莊稼人,和黃土打交道一輩子,大字不識幾個,但崇敬文化和讀書人。每年臘月二十三大清早,先把大門門窩的“耕讀第”擦洗幾遍,再把中堂上的朱子家訓灰塵撣拂干凈,才開始做過年的準備。來年正月初二又誠請莊里幾位有學問的老太爺在家薄酌。談論些“藜豆花開蟋蜶鳴,讀書勝樂樂何如”的話題,目的是耳濡目染我爺,看能否走點科考的前程。我爺筆管似的站一旁恭聽。
我爺聰明固執、勤苦節儉,四季穿著補丁衣裳,長年吃著高粱面饃,是有名的“細磨石”。他種的一手好棉花,酷愛讀書,一邊種著棉花,一邊隔三岔五背上干糧,走三十里路來到天水城張育老門下聽講。1905年科考廢除了,他老學而優則仕的愿望破滅,但他不仕不優則學,晚上一盞油燈掌本書看到深夜,耕讀并進兩不松手。我婆去世早,他老掌管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總對著“耕讀第”的大門看了又看,不甘心啊,覺得對不住先輩的“讀”字,沉思了半年,最后牙一咬,用積攢了幾年的錢,在鄉紳舉薦下給自己捐了個貢生,得了一身頂戴,雖是虛名,但滿足了他老多年愛讀書的心理,也對得起老祖宗的這個門窩。逢年過節,來人客氣,他老享受著貢老爺的幾個響頭。出門進門總罵著一句話,“一寸光陰一寸金,寸金難買寸光陰,唉、唉!”好像全家大小十幾口人都入不了他的法眼,逼得孫子們故作學習狀。現在若回頭看,在他老的影響和呵斥下是有好處的。多年后我伯家的我二哥是有名望的教師,前些年天水進行高考前模擬高考考試,他是出題人之一;我三哥是西北師大生物系的畢業生,后留校任教;我四哥是西安醫學院的畢業生,是外科大夫。我爺1948年去世,因我出生晚所以沒見過。但我多年后看到他老留下的遺產,就是寫給廣應山草屲的一副對聯:“草坡巒上紫竹林節節疏通天下士;廣應山間白仙鶴聲聲喚醒夢中人。”
川里老輩人還注重從小傳承耕讀古意,記得我小時候,給遠房的舅爺拜年,舅爺樂觀開朗、待人和善,我們尊稱長爺。磕頭后他把我叫到大門口,給我講他寫的春聯,“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說到臂字時,胳膊還甩了兩下。一抬頭便講解“耕讀第”三個大字,引經據典,趣味十足,又倒過來說“第讀耕”的含意,通透有趣,覺著生動得很。再走到正房的大窗前站好,一格一格地講上面的印版窗畫24孝圖案,48格窗畫他講得精彩傳神,我聽得津津有味。但窗子底下的炕眼門絲絲冒煙,嗆得我倆咳嗽,熏得我淌眼淚,他老講的鼻一把淚一把,我聽的鼻一把淚一把。他老有學識,講的故事好像就發生在窗子跟前,栩栩如生,印象深得很,我年齡小竟然全部記住了。
三陽川的兩條河撥轉著磨坊,流淌著希望,也磨煉出人的生活走向,就是自己甘心勞累,要讓兒女潛心念書,土話叫“務人哩”。因為人均地少,人們除了種莊稼外,還要做些農本生意,換些油鹽錢,其實主要是湊足兒女們念書的盤纏。原正陽寺旁的坡口有座門樓,是三陽川生意擔進出天水城的必經官路總門,懸著兩面大匾,西面是“三陽開泰”,某州官的親筆;東面是“羲皇故里”,南岸某文人的敬題;配聯是南岸楊老爺的撰書,“薄地能耕犁云鋤雨;新書耐讀戴月披星”。這門里每天不分黑明晝夜,人來人往。三陽川人心里樸素,卻能算大賬,只要供給娃娃把書念成,有了出息,將來就省得蓋房子,就免得費周折娶媳婦。說不定到城里還當縣長呢!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從“耕讀第”大門里出進的是菜水擔、瓜果擔、豆腐擔、掛面擔;背篼里、包袱里的是棉花、土布、棉線。走進村莊,一聽是織布聲、紡線聲,他們正在編織著那些背書包娃娃的大學夢呢!
三陽川人目的明晰,各自人等找錢的路徑不同,其理一也。木匠緱師、牛師,他們的兒女都在上大學,做活名氣大能走藝四方,大門蓋得翹勢騰升、典雅大方,家里藏有門窩“耕讀第”可臨的五六個版本,又備有專用刻字工具,刻工也精到一流。前些年朋友茂子家翻新大門,就請的是牛師。我們到他家去選好中意的“耕讀第”三字,他就加夜臨摹了。刻門窩是個大手藝活,不同于印章的陰紋、陽紋,門窩要體現立體感,融合多種雕刻技法,講究字邊深入,筆畫凹凸奇宕,最見功力的是飛白,如“讀”字的點,“第”字的竹頭,牛師刻“耕讀第”用了七八種工具,花了兩天多時間。“耕讀第”才刻描填漆成功,還要“放盤”上位,本來平整光滑鮮亮,合適哩!但有人喊“盤斜了”,茂子趕緊用幾張10元的票子往盤底一墊,“平了平了”牛師哈哈一笑,把錢一收。鞭炮一響,立門一新,“耕讀第”三字氣派橫云,門聯是:周公卜定三吉地;魯班造就五福門。這就是三陽川普通人家的“耕讀第”文脈傳承。
十年前的某天,我休假無事,騎自行車順川道趕集,沿途看些大門上“耕讀第”的書法風格,走到石佛一郭姓人家門口,看似新大門,門窩卻有些發舊,也想討杯水喝,就搭訕著進去了。主婦和婆婆操持家務,主人到蘭州打工開鏟車去了,兒子在成都讀研,女兒在江西上大學,主婦養雞,還要務果園。她說:“唉,辛苦得很啊,就是心里有些盼頭。”坐下看見中堂掛的是《松下課孫圖》,配聯是:春風放膽來梳柳;夜雨瞞人去潤花。我問門窩為啥有點舊,她說:“那是舊門上的,棗木的挪過來了,是先人早些年用三個銀元臨刻來的,他爸舍不得丟,就用上留個念想。”我想給她們在“耕讀第”門前照個相,她說:“唉,不敢,書沒念好。”只得身后掛了幾串辣椒作背景。
“耕讀第”鼓勁了川里人勤苦的勞動本色,勉勵了莘莘學子的發奮有為。
自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從三陽川“耕讀第”門下,走出了一兩萬大中專、職業技校學生,他們偏重報考師范類、醫學類專業。現在,如春節返鄉過年,從四面八方,跨進家門看望父母,闔家團聚的大多是拖家帶口的文教、醫護人員。其中像“連中三元”“一門四進士”的并不稀少,“五子登科”的也能找出八九家。
“耕讀第”是三陽川莊戶人家的文化基因!
相關新聞
- 2021-12-16于家柯寨并蒂柳
- 2021-12-16文明交匯地敦煌:絲綢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 2021-12-16《地理·中國 在河之州》第三集《叩問遠古》
- 2021-12-16《絲路非遺》看渭源花兒和羌蕃鼓舞